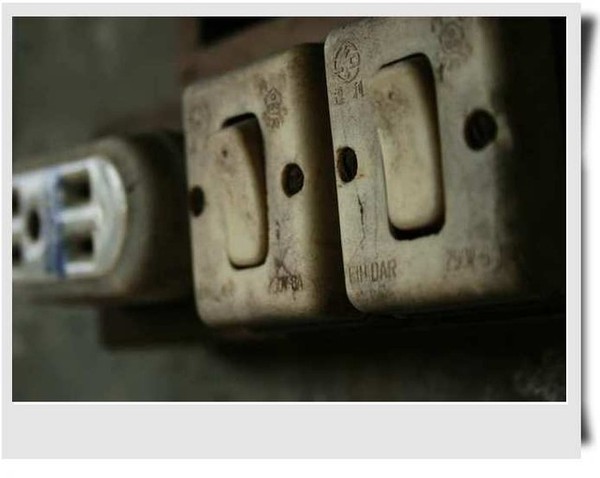
事實上,我不是很清楚他是從哪個方向出現在我眼前的了。
星期天下午四點,南方小村莊的炙熱讓人只能在汗流與口渴之間選擇一個去專注,在我和球友G用很生嫩的網球球技來回比劃了一小時後,一旁休息的我倆選擇了牛飲沁涼的礦泉水,至於那止不住的汗水就讓它流吧,甚至,G把上衣都脫了,那水珠要在空氣中慢慢揮發或是延著他的胸口一路流到褲襠都無所謂了。
就在我倆討論剛剛的對打結果時,G的好友剛好帶著他的小兒子閒晃到球場來。
他就是這麼出現的。
其實,大家都是年紀相仿的同鄉,所以一開口就是用客家話聊個沒完也沒什麼好奇怪的,而我和G也適當地在當下跳開網球這個話題,至於那位三歲大的小朋友則拿著拍面比他臉龐還大半倍的球拍揮舞著。
「我跟你一起打好不好?」我問。
「真的嗎?好啊,不過我不太會打啦。」
我不是對他的謙虛感到訝異,而是這位在我眼前舞動的小朋友竟然用很流利的客家話和我對話著,那種面對面的驚詫讓我一時語塞,彷彿他只是個長不高的鄰居叔叔,我甚至懷疑這個小不點不知國語為何物。
當然,這裡不是要要討論族群意識的問題,我也不想。
我只是想著我怎麼和大人們用客家話對話的小時候罷了。
就像妳起初不相信我會講客家話一樣,事實上,妳無須訝異我的孩童歲月都在勞動歲月中度過的。
那種勞動是很真實的,或許因為我幾乎不知道玩樂為何物(在三合院前掃地時拿掃帚當刀劍算不算);那種勞動好像又是無邊無際的─稻田、檳榔園、豬舍、鴨寮,甚至那座永遠有著掃不完鋁屑的鋁門窗工廠等等都是我的遊樂場。
我一直以為那就是童玩歲月,我以為勞動就是玩樂,帶著一點苦。
「哇,你小時候做過的事都是我爸媽以前做過的。」妳這麼說著。
這樣的相對比較似乎是挺可怕的,尤其反映在年紀這件事情上面時,然而,我卻不擔心妳嫌我老氣,儘管妳我偶而說著不同的語言,然而,慢慢地,妳詫異的將不會再是我流利的客家語,而是那段慘綠年少,妳從未觸及的。
全站熱搜


 留言列表
留言列表